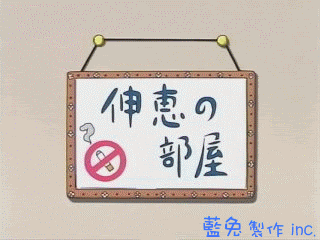- 註冊時間
- 2006-8-27
- 最後登錄
- 2024-3-8
- 主題
- 查看
- 積分
- 1397
- 閱讀權限
- 110
- 文章
- 127
- 相冊
- 0
- 日誌
- 0
   

狀態︰
離線 
|
@@"
1948年的長春圍城慘劇
慘過所謂南京大屠殺.
當時,長春圍困戰前,居民約50萬左右!五個月的圍困,全城七百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部分,大到房架,小到交通標志牌,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盡情地送入口中,化作維係呼吸運動的熱量,戰後長春只剩下十七萬人...真的是淒慘無比!
一是存有幻想,二是顧及軍心士氣面子,圍困之處,國民黨不準百姓離城。尚傳道提出“人人種地,日日練兵”,號召軍民同舟共濟,保衛長春。鄭洞國講台灣正在訓練大批美械新軍,即將開赴東北大舉反攻,只要守住半年左右,大局能扭轉。
幻想成為幻想,口號只是口號。即便人手一把鋤頭,掘去瀝青的馬路能長莊稼,也得等到秋後才能吃到嘴裏,而存糧只能吃到七月底。五十萬張嘴,成了國民黨的沈重負擔。
七月下旬,蔣介石致電鄭洞國,從八月一日起,疏散長春哨卡內人口,只準出卡,不準再進。
長春圍城是指發生在中國國共內戰時期的長春圍困戰期間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事件。
1948年,林彪率領的中國共產黨東北野戰軍對國民黨政府軍控制的長春城實行圍困,6月5日,林彪、羅榮桓下達《圍困長春辦法》,決定對長春實行「久困長圍」方針。要求採取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手段,圍困長春。長春圍城歷時五個月。造成大批城內平民因饑餓而死亡。全城700余萬平方米建築,230萬平方米被破壞。一切木質結構,乃至瀝青路面,或用於修築工事,或充作燃料,而一切可以當做食物的東西,如樹皮、樹葉之類,都被吃光。
在圍城的初始階段,國軍曾限制居民外出,但後因城中發生饑荒,隨對居民放行,並限制其返回。其間也發生國軍士兵搶奪居民糧食的現象。對企圖逃出長春求生的平民,共軍開始曾進行搜查審問後放行,但僅限於帶槍投靠的國民黨人。「他們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將嬰兒小孩丟了就跑,有的持繩在我崗哨前上吊。戰士見此慘狀心腸頓軟,有陪同饑民跪下一道哭的,說是『上級命令我也無法』。」後來採取了圍阻「捆綁」以及射殺的行動。大批饑民被迫滯留在兩軍控制的環城中間地帶,其間遍佈腐爛的餓死民眾的屍體。據一些當事人的回憶證實,圍城期間包圍圈中曾發生食人悲劇。圍城最後以國民黨軍投降而告終。「當年參加圍城的一些老人說:在外邊就聽說城裡餓死多少人,還不覺怎麼的。從死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見多了,心腸硬了,不在乎了。」「可進城一看那樣子就震驚了,不少人就流淚了。」解放軍士兵看不下去,有些人問「咱們是為窮人打天下的,餓死這麼多人有幾個富人?有國民黨嗎?不都是窮人嗎?」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雪白血紅·第三十一章 「兵不血刃」》)
長春的居民人口由圍困前的50萬左右(包括圍城前從周圍地區逃至長春以躲避戰亂的難民)銳減到圍城後的17萬人。餓死居民的人數,目前尚無確切統計。作家解放軍中校張正隆在《雪白血紅》里分別引用時任長春市長尚傳道的回憶錄稱「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和國民黨《中央日報》戰後的報導稱城外「屍骨不下十五萬具」;日本媒體的估計為二十至三十萬人(戰前滯留長春的日本人約3千,據說其中很多戰後被餓死)。1975年被釋放的戰犯段克文在《戰犯回憶》一書中說,長春圍城餓死了六十五萬。
國民黨方面認為,中共軍隊在圍城期間的行為構成戰爭犯罪;共產黨方面則認為其軍隊為「解放」長春而採取的行動是正義和積極的,造成饑民死亡是次要的,在中共官方宣傳口徑中,有「兵不血刃取長春」之說;而很多非國共人士及國際輿論則認為,長春圍城是二十世紀最慘重的戰爭災難之一。
八月十七日,一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唐天際,在圍城部隊高幹會議上的報告中說∶
在圍城時期,基本上還是執行圍困封鎖,禁止人民與長春市之來往,禁止與長春之貿易關係。但在我警戒線附近,因蔣匪之搶掠驅逐與強制疏散而奄奄待斃之饑民很多,死亡率很大。這些人已經不可能回到長春市內增加敵人之負擔,故我們還是必須加以救濟。這對我們的政治影響及部隊的影響是很大的。關於放出與救濟這些難民有以下幾個原則∶
甲、難民已進入警戒線內及警戒線外附近之地區,或我軍攻占之地區,對是饑餓死亡很嚴重者,放出或予以就地救濟,至於城內及敵乘隙新疏散出來之難民則暫不能救濟,待調查之後聽候處理,對於尚存有糧食,或將存糧出賣者不予放出。
乙、不是大批號召及整批自流的放出,而是在部分地區(即指定一定的放行之道路)采取部分的放行,故可先派工作人員進入難民地區進行調查,將真正的難民予以組織,告以放行之時間地點,並予以證明,每一期預計放行之數目要先期報告,以便準備救濟。
丙、在放出之難民中,工人與學生可以吸收者經難民處理委員會轉至適當地點收容,但不是號召城內工人學生都出來。對於真正有特殊技術之人才,可以號召爭取其出來,亦送委員會。
九月九日,“林羅劉譚”在給毛澤東的報告中說∶
我之對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線上五十米設一哨兵,並有鐵絲網壕溝,嚴密結合部,消滅間隙,不讓難民出來,出來者勸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後來饑餓情況愈來愈嚴重,饑民變乘夜或與白晝大批蜂擁而出,經我趕回後,群集於敵我警戒線之中間地帶,由此餓斃者甚多,僅城東八裏堡一帶,死亡即約兩千。八月處經我部分放出,三天內共收兩萬余,但城內難民,立即又被疏散出數萬,這一真空地帶 又被塞滿。
白 骨 之 城
“兵不血刃”的長春之戰,把手無寸鐵的老百姓推上了第一線。
尚傳道在回憶錄中寫道∶“根據人民政府進城後確實統計,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報》在一篇《長春國防守經過》中寫道∶“據最低的估計,長春四周匪軍前線野地裏,從六月末到十月初,四個月中,前後堆積男女老少屍骨不下十五萬具。”
長春變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餓殍之城,白骨之城。
宋占林∶
死人最都的洪熙街和二道河子。洪熙街什麼樣子沒見到,二道河子十室九空。開頭還弄口棺材,接著是大櫃、炕席甚麼的,後來就那麼往外拖也沒人幫忙了。都死,誰幫誰? 拖不動了,就算到地方了,坐那兒就動不了了,也死那兒了,最後也沒人拖了。炕上,地下,門口,路邊,都是。有的白花花剩付骨架,有的正爛著,剛死的還像個好人。大夏天,那綠頭蠅呀,那蛆呀,那味兒呀。後來聽城外人說,一刮風,十裏、八裏外都燻得頭痛。
我們家附近沒一家不死人的。同院的王青山,五口剩一口。西邊何東山,也是五口剩一口。前院一個姓曾的木匠,七口人剩個老伴。“楊小個子”一家六口,剩個媳婦。後邊一家“老毯兒”(東北號稱闖關東的河北人為“老毯兒”),六口全死了。
舊曆八月初,我臨出哨卡走到現在膠合板廠那兒,想喝點水。一家門窗全開著,進去一看,十多口人全死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炕上有的還枕著枕頭,女的摟著孩子,像睡著了似的。牆上一只挂鍾,還“嘀嘀嗒嗒”走著。
開頭見死人掉眼淚,頭皮發炸。後來也害怕,不是怕死人,是覺得自己早晚也是這條道。再往後見了打個唉聲就過去了,再往後再往後連個唉聲也不打了,也不把死當回事兒了。
解放後,熟人見面就問∶你家剩幾口?就像現在問∶你吃飯了嗎?
解放後第一件事就是“救生埋死”。“救生”就是給活著的發糧食,“埋死”就是埋死人。我參加“埋死”了。幹一天給五斤高粱米,幹了個把月。全城都幹,全民大搞衛生運動,不然發生瘟疫更了不得。挖個大坑,把鋼軌甚麼的架上,屍體放在上面燒。大部分是埋的。有的集中一起挖個大坑埋,有的隨處挖坑就埋了。前院姓曾的一家都爛炕上了,拿不成個了,唉,別說了。第二年看吧,凡埋死人的地方都不長草,那地太“肥”了。
吉林省軍區原參謀長劉悌,當時是獨八師一團參謀長。
《 本帖最後由 DarkRobert 於 2007-6-10 20:45 編輯 》 |
-
總評分: 威望 + 1
查看全部評分
|